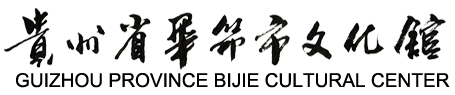|
黔西北墓雕艺术浅析时间:2017-06-19 早在五、六十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开发了黔西北这块古老的土地。这里居住着汉、彝、回、苗、布依、仡佬、水、满、白等十多个民族。他们创造了不同风格的文化艺术,其中墓雕艺术,就是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墓雕艺术的形式丰富多彩、具有较高的装饰性、实用性、和艺术性。黔西北墓雕艺术形式不仅可以直接地或间接地反映各个历史时期各民族的社会风貌,而且就其雕刻技巧上来讲,概括地反映了我国古代石刻艺术的水平。 黔西北的墓雕石刻,经历了一漫长的历史阶段。东汉后期,佛教流人中国,墓雕艺术的形式便随之而产生。早期的墓雕石刻、是以刀代笔在砖石面上作线刻画,由于是雕刻在砖石上的面的画、所以又把它称之为画像石。汉代的画像石是我古代文化遗产的瑰宝,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在黔西北的赫章可乐汉墓群、威宁中水汉墓群和毕节、黔西等地,已经相继发现了不少汉代的画像和陶塑砖。画像砖雕刻艺术形式古朴凝重,均采用石勒制、线刻和浮雕等不同技法。题材多样,有“春耕图”、“狩猎图”、“车马图”以及几何纹等。画像砖石的特点是以绘画雕刻的艺术形式,生动形象的描绘记录了的社会生活,宛如当时社会意识形态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当时的意识形态。鲁迅先生曾评论汉代的石刻画像是“深沉雄大”。汉代画像砖石图案,在雕刻艺术中的一鳞一爪,美妙绝伦。汉画像砖石本身就是一种绘画雕刻艺术,在我国雕刻史上有着重要地位。 黔西北地区,曾出土过大量的汉代陶塑,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明器,种类有器皿、建筑模型、人物、动物等。赫章可乐出土的干栏式建筑模型,是用梁柱构成一个座架,承托上面的房屋。房屋下面架空,并安有加工粮食的碓。这是一件很重要的资料,说明黔西北地区古代也曾经有干栏式建筑,只是今天已经不存在了。毕节城郊曾出土过几个厅堂建筑模型,与川西出土的建筑模型相似,它的背饰同云南地区在文化上的关系很密切。黔西出土的陶俑,包括乐俑、家禽等,造型古朴,制作较粗,火候也不高,但形象仍然很生动。 汉代以后,在黔西北地区发现的有唐宋时期的墓雕石刻。这一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在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文化艺术等诸方面都相继发展到了顶峰的时期。石雕艺术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由于思想文化的发展,各种教派组织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各种宗教的石刻、儒家的石刻及雕刻艺术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据《凡将斋金石丛稿》载:“……隋唐承北朝之余风,事无巨细,多刻石以记之,自是以后,又复大盛,于是石刻文字几遍全国矣”。这一时期的书册,石工镌字,均署名,名人、名士、名僧无不竞相笔札册书石上,由于黔西北地处西南边陲的少数民族地区,当时,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是在文化等方面,都远落后于发达的中原地区。这一时期的墓雕石刻、仅在金沙、黔西两县,发现了零星几处的墓碑石刻。其艺术特点,主要流于线刻,也有少量的浮雕图案。刻画内容多为梵文符号,反映宗教意识。雕刻特点,庄重典雅,落笔细腻。 黔西北的墓雕石刻,大都集中在明清两代,经过近年来的文物普查,据不完全统计,现已发现明清时期较有艺术价值的墓雕石共计384处。 元代以后,随着各族人民的不断迁徙、相继定居于黔西北地区。由于他们带来了中原汉族地区的先进文化,从而在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方面都有了新的发展,墓雕艺术也随之而发展。当中原的石刻艺术正趋于衰落之时,黔西北的各族人民继承并发展了这一古老的传统文化,使石雕艺术又重新在墓雕艺术上焕发生机。 这一时期,在黔西北地区、由于封建的地主经济的发展和其享乐生活的本质所决定,认为“孝乐",才是“忠君”。而“孝”的突出表现是奉行厚葬,并以厚葬为手段来博取“孝子”的美名。于是便形成了“世以厚葬为德,薄终为鄙”的社会风气。不仅豪门贵族如此,就连一般百姓也竞相仿效。在越来越多地仿效地面住宅营建地下墓室的发展趋势中,官殿的壁画形式也很自然地用到了地下的墓雕艺术上。从而实现了封建贵族们的享乐生活,以及用各种雕刻技巧来表现天下地下与历史现实,可谓无所不包,从而一个琳琅满目的现实世界在墓雕艺术中展现出来。 黔西北明清时期的墓雕石刻,是一部伟大的古典现实主义作品。它在雕刻技法上,继承并发展了我国石刻的优良传统,对线条的运用趋于成熟,对形象刻画的准确有较强的概括性,表现了事物的性格、特征和动律的感觉。在反映线刻作品中,最丰富的墓雕石刻,要数黔西县的“宋家沟花坟”了。它用规则弧形料石36块砌成,采用线刻及凸面减地雕图案72幅,匀称地镌刻在每头石面上。雕刻多以各民族的社会风俗为题材:有“跳花坡,咂酒、舞龙、花灯、踩索桥、吹芦笙、说书唱戏、庭院杂要”等欢乐场面。 再从大方、金沙的“满族花坟”来看,墓雕技法,均采用凹凸线刻结合、减地处錾麻纹(满天星),加以烘托渲染,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画面多采用动植物构图,异于他族。碑上多透雕龙凤、连环双线、花瓶、兼满文印章、铭文。雕刻艺术上来看,“宋家沟花坟”和“满篓苎挚”,有许多图案显示了很高的艺术水平,它突破了古代抽象图案化的概念,具有明显的写实倾向和浓厚的生活气息,在现实主义的作品,同时也反映了明清时期的民间工匠对生活的熟悉和对事物的洞察及概括能力。 黔西北的雕刻石艺术的精品应首推“金沙敖家坟墓群石刻”和“织金方家坟石刻”。两处墓雕形制大体相似,其雕刻技艺各具风采。“敖家坟墓群石刻”墓群依山布局,分南北两墓群。南墓群分四层台、逐级升高。南、北墓群外由山门、棚栏、照壁墙垣组成,内筑石墓二重三座。南北墓群的牌楼均布满雕刻.有“狮鹿麟兽”“猪马牛羊”“活佛仙人”“花鸟鱼虫”“车马出行”“征战出巡”“牛耕放牧”“河流山川”等图案。从基座到柱础、从抱鼓到额枋、屋面瓦沟、照壁墙面、山墙脊顶,共雕有不同画面1102幅。可谓“无面不雕、无空不琢"。雕有人物1 080个、马90余匹、动植物30多类、花卉50余种、书法百余件、楷行草篆共三千多字。其中上乘之作,要数南墓群左右侧照壁中“征战图”和“空城计",它采用半镂半浮雕的技法,刻画的马,千姿百态、把圆润肥大的身躯和瘦劲刚毅的四肢结合起来,不但没有不合适、不相称之感,反而感觉到那样的身躯就应当是那样的四肢,肥美与刚毅融洽合一,成为真正的骏马铁骑。刻画人物、以寥寥几笔勾勒出人物的面目,生动传神、形象丰满、使人物形象奇古。刻画飞禽走兽,构思奇巧,主体突出,夸张适度,极富新意。它不仅表现了艺术上的夸张,而且更表现在刻画那些山神海灵、奇禽异兽人世间没有的东西,这是由于工匠艺术家充分发挥了想像力和创造力,把人和动物的各部位有机的结合在一起,赋于禽兽以人格化的形象。把人和动物插上翅膀,有平列诸物的形象、满幅而天的感觉,给人的感觉是丰满朴实而充满活力的意境。 而雕刻技法上,多彩用镂透、浅浮雕、高浮雕等技法。它融书法与绘画为一体,舒展而不零乱、写意而不失真,并在写实的基础上,真中蓄幻,幻中见意,惟妙惟肖。达到了完整和谐统一,令人叹为止。 “织金方家坟”墓雕艺术,它以阳刻高浮雕、镂、透雕为雕刻的主要技法,把“书匾”及柱上“动而欲出的龙、人物、狮鹿麟象”等像,分别雕在墓枋的实出部位,体现了“力”的气魄,“动”的体态。以方国玺的墓枋为例,它以大胆的造型、夸张的手法,使整座牌楼都布满了高浮雕和镂透雕,中柱是镂空盘龙而上双行龙,其雕刻之处,无论是远看、近看、仰视、俯视、上下左右都呈现出一幅瑰丽精巧的木形图案。在大额仿、小额枋、匾额、屋檐、顺弥座等处,无一不 见精雕细刻、美轮美奂的艺术作品。它们时而用浅浮雕、时而用高浮雕、或用镂空剔透、或雕镂结合。用笔圆润,点划分明,铺排妥帖,行款井然,巧妙生动。刻画的内容有历史故事、有文武百官、兵卒僮仆、栩栩如生。楼台亭榭、山水小桥,细致精巧,显示了明清匠师的艺术匠心。他们在创造具体物象时,不拘泥单纯的模似,而是大胆运用艺术的夸张,突出的是高度夸张的形体姿态,是手舞足蹈的大动作、或是单纯简洁的整体形象。对各种人物的形体、姿态的夸张,特别是对各种动物的形象,不一定符合写实的标准,而经过夸张的手法刻画出来的,长身、大眼、短足的动物,更显得英姿和凶猛有力。如果说唐代艺术更多的表现了中外艺术的交融,那么,黔西北墓雕艺术却更突出地呈现民族文化的特色。 一幅幅玲珑剔透的墓雕艺术作品,它题材广泛,内容丰富、生动,概括地描绘了黔西北地区历代的社会风貌和历史文化。这是民间艺术家根据他们的亲身生活的体验和观察,通过石刻画像把当对社会生活现象如实地反映出来。其中“吹芦笙”、“踩索桥”、“咂吾”、“农耕放牧”等,都反映了黔西北各族人民浓厚的生活习俗和经济特点。 由于封建统治者大肆宣扬死后灵魂可以升天,愚弄了广大劳动人民。他们梦求“生死同乐”,不惜抛出人力物力,集八方能工巧三,大肆修葺“人间天堂”。这些不朽的古典写实墓雕艺术作品,对开究黔西北的历史、民族学、艺术史等,都有着相当重要的价值。 |